译文及注释
译文
白云掩没边塞险要的城堡漫卷而来,昏暗的烟尘从天边浮起。
关山的四面已把行路阻绝,遥远的故乡又何止几千里。
注释
断句:近似于绝句,通常四句。
鄣(zhāng):边塞险要的城堡。
绝:堵绝。
赏析
这首诗的前三句写景,描写了白云漫卷,烟尘四起,关山阻绝的惨淡景色;后一句抒情,表达了远离家国的悲伤和担忧。全诗语言悲慨,感情真挚。
刘昶在宋不以诗名,这首《断句》是他流传下来的唯一诗篇。这首诗同项羽的《垓下歌》一样,具有撼山动地的感人力量。平时不知书的项羽在重兵围困、四面楚歌的情况下,面对宝马美姬,悲从中来,慷慨而歌,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绝唱。刘昶也是在有国难投、有家难奔的绝境之中,唱出这悲壮激昂,左右莫不哀哽的悲歌的,这是诗人真实感情的流露。况周颐在《蕙风词话》所说的:“真字是词骨,情真景真,所作必佳,且易脱稿。”也就是指的这种情形。
刘昶在自己的国家里无法立足,不得已仓惶出逃,而所投奔的恰恰又是自己的敌国,此去的前途危险难测,或许,等待着他的也是杀头。尽管如此,自己还必须尽快往前赶,因为后路已经断绝,向前毕竟还有一线生机,这渺茫的希望在激励着他一路狂奔。身陷绝境的刘昶,当时的惶急悲愤是不言而喻的。诗的前三句,集中笔力,以浓重的色彩,描绘出刘昶奔亡途中的景物:白云从群峰迭嶂里涌出,尘土遮天蔽日而起,四面山势陡峭,道路断绝,前途是如此暗淡,周围是如此险阻,正是诗人当时处境的形象描绘。“一切景语皆情语也。”(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)此时四周的景致,实际上也正是刘昶此时心情的写照。面对如此惨淡的景物,顿时激起诗人内心感情的波涛。故乡,自己生长爱恋的地方,如今就要一朝远离,也许永远也见不到了,而自己的妻子和母亲,都还留在故乡,生死未卜,这就更加增添了诗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和担忧。 “故乡几千里”,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悲愤呼声。
这首诗不以词藻妍丽取胜,而以悲壮激越的声调感人,“天予真情,发言自高。”(皎然《诗式》)刘昶为当时情势所激,将满腔悲愤随口倾吐,无暇雕饰,反使此诗成为绝唱,这在日趋华靡的刘宋诗坛尤其显得难能可贵。刘宋时期,诗坛虽然初步摆脱了玄言诗的桎梏,但很快又染上了追求词藻典故的风气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曾指出当时诗人“俪采百字之偶,争价一句之奇,情必极貌以写物,辞必穷力而追新”的不良倾向。钟嵘也批评“大明泰始中,文章殆同书抄”(《诗品序》)。刘昶的《断句》却能不受当时诗风的影响,直接继承“左思风力”(钟嵘《诗品序》)和刘琨悲壮清刚之气,从而使这首诗表现出了与当时诗风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。
这首诗在写法上也具有独特之处,并给唐人以直接影响。“断句”亦即“绝句”,是唐人绝句的滥觞。唐人绝句有不少是效法六朝的。李白的《越中览古》:“越王勾践破吴归,战士还家尽锦衣。宫女如花满春殿,只今惟有鹧鸪飞。”沈德潜曾评道:“三句说盛,一句说衰,其格独创。”但李白此诗在格式上有着刘昶《断句》的明显影响,只是将刘诗的“三句写景,一句抒情”换成了“三句说盛,一句说衰。”这种格式不同于一般绝句的写法,不是在绝句的第三句而是在末句才转换辞意。诗人要竭尽全力在前三句中将诗意的一方面写尽写透,以便积蓄力量,满弓待发,然后笔锋突然一转,在结句将主题跌出,从而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诗人的思想感情,同时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这种写法需要诗人具有扭转千斤的大力量,大气概,在绝句的创作中无疑是独特的,但首创这种格式的,不是李白,而应归之于刘昶。▲
创作背景
刘昶是南朝宋文帝的第九个儿子,元嘉中封义阳王。宋废帝子业继位,为徐州刺史。废帝刘子业是个凶淫过于桀纣的暴君,继位后大肆屠戮宋室宗亲和朝臣,刘昶也是他准备捕杀的对象。据《南史·刘昶传》载:废帝派大军征讨刘昶,“昶即起兵,统内诸郡并不受命,昶知事不捷,乃夜开门奔魏,弃母妻,唯携妾一人,作丈夫服,骑马自随。在道慷慨为断句曰:‘白云……’因把姬手,南望恸哭,左右莫不哀哽,每节悲恸,遥拜其母。”
据此可推此诗作于永光元年(465年)九月。
刘昶(436年-497年),字休道,南朝宋宗室,北魏将领,宋文帝刘义隆第九子,宋孝武帝刘骏、宋明帝刘彧异母兄弟。母谢容华。刘昶虽流亡北魏,但始终不忘故国,在南齐篡立后多次引魏军南下,希望借助北魏的力量恢复祖业,但均未能成功。他于太和二十一年(497年)病逝,终年六十二岁,追赠太傅、扬州刺史、谥号明。
余幼时即嗜学。家贫,无从致书以观,每假借于藏书之家,手自笔录,计日以还。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可屈伸,弗之怠。录毕,走送之,不敢稍逾约。以是人多以书假余,余因得遍观群书。既加冠,益慕圣贤之道,又患无硕师、名人与游,尝趋百里外,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。先达德隆望尊,门人弟子填其室,未尝稍降辞色。余立侍左右,援疑质理,俯身倾耳以请;或遇其叱咄,色愈恭,礼愈至,不敢出一言以复;俟其欣悦,则又请焉。故余虽愚,卒获有所闻。
当余之从师也,负箧曳屣,行深山巨谷中,穷冬烈风,大雪深数尺,足肤皲裂而不知。至舍,四支僵劲不能动,媵人持汤沃灌,以衾拥覆,久而乃和。寓逆旅,主人日再食,无鲜肥滋味之享。同舍生皆被绮绣,戴朱缨宝饰之帽,腰白玉之环,左佩刀,右备容臭,烨然若神人;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,略无慕艳意,以中有足乐者,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。盖余之勤且艰若此。
齐宣王问曰:“齐桓、晋文之事,可得闻乎?”
孟子对曰:“仲尼之徒,无道桓、文之事者,是以后世无传焉,臣未之闻也。无以,则王乎?”
曰: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?”
曰:“保民而王,莫之能御也。”
曰:“若寡人者,可以保民乎哉?”
曰:“可。”
曰:“何由知吾可也?”
曰:“臣闻之胡龁曰:‘王坐于堂上,有牵牛而过堂下者,王见之,曰:“牛何之?”对曰:“将以衅钟。”王曰:“舍之!吾不忍其觳觫,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”对曰:“然则废衅钟与?”曰:“何可废也,以羊易之。”’不识有诸?”
曰:“有之。”
曰: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,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王曰:“然,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,吾何爱一牛?即不忍其觳觫,若无罪而就死地,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曰: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,彼恶知之?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,则牛羊何择焉?”
王笑曰:“是诚何心哉!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,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曰:“无伤也,是乃仁术也!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:见其生,不忍见其死;闻其声,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
王说曰:“《诗》云:‘他人有心,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,反而求之,不得吾心;夫子言之,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?”
曰:“有复于王者曰:‘吾力足以举百钧,而不足以举一羽;明足以察秋毫之末,而不见舆薪。’则王许之乎?”
曰:“否!”
“今恩足以及禽兽,而功不至于百姓者,独何与?然则一羽之不举,为不用力焉;舆薪之不见,为不用明焉;百姓之不见保,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,不为也,非不能也。”
曰: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,何以异?”
曰:“挟太山以超北海,语人曰:‘我不能。’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,语人曰:‘我不能。’是不为也,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,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;王之不王,是折枝之类也。”
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;天下可运于掌。诗云:‘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,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,无他焉,善推其所为而已矣!今恩足以及禽兽,而功不至于百姓者,独何与?权,然后知轻重;度,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,心为甚。王请度之。抑王兴甲兵,危士臣,构怨于诸侯,然后快于心与?”
王曰:“否,吾何快于是!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
曰:“王之所大欲,可得闻与?”
王笑而不言。
曰:“为肥甘不足于口与?轻暖不足于体与?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?声音不足听于耳与?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?王之诸臣,皆足以供之,而王岂为是哉!”
曰:“否,吾不为是也。”
曰:“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:欲辟土地,朝秦、楚,莅中国,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,求若所欲,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
王曰:“若是其甚与?”
曰:“殆有甚焉。缘木求鱼,虽不得鱼,无后灾;以若所为,求若所欲,尽心力而为之,后必有灾。”
曰:“可得闻与?”
曰:“邹人与楚人战,则王以为孰胜?”
曰:“楚人胜。”
曰: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,寡固不可以敌众,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,方千里者九,齐集有其一;以一服八,何以异于邹敌楚哉!盖亦反其本矣!今王发政施仁,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,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,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,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,天下之欲疾其君者,皆欲赴愬于王:其若是,孰能御之?”
王曰:“吾惛,不能进于是矣!愿夫子辅吾志,明以教我。我虽不敏,请尝试之!”
曰: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,惟士为能。若民,则无恒产,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,放辟邪侈,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,然后从而刑之,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,罔民而可为也!是故明君制民之产,必使仰足以事父母,俯足以畜妻子,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于死亡;然后驱而之善,故民之从之也轻。今也制民之产,仰不足以事父母,俯不足以畜妻子,乐岁终身苦,凶年不免于死亡;此惟救死而恐不赡,奚暇治礼义哉!王欲行之,则盍反其本矣!五亩之宅,树之以桑,五十者可以衣帛矣;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;百亩之田,勿夺其时,八口之家,可以无饥矣;谨庠序之教,申之以孝悌之义,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,黎民不饥不寒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”
愈再拜: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。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。贫贱也,衣食于奔走,不得朝夕继见。其后,阁下位益尊,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。夫位益尊,则贱者日隔;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,则爱博而情不专。愈也道不加修,而文日益有名。夫道不加修,则贤者不与;文日益有名,则同进者忌。始之以日隔之疏,加之以不专之望,以不与者之心,而听忌者之说。由是阁下之庭,无愈之迹矣。
去年春,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。温乎其容,若加其新也;属乎其言,若闵其穷也。退而喜也,以告于人。其后,如东京取妻子,又不得朝夕继见。及其还也,亦尝一进谒于左右矣。邈乎其容,若不察其愚也;悄乎其言,若不接其情也。退而惧也,不敢复进。
今则释然悟,翻然悔曰:其邈也,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;其悄也,乃所以示其意也。不敏之诛,无所逃避。不敢遂进,辄自疏其所以,并献近所为《复志赋》以下十首为一卷,卷有标轴。《送孟郊序》一首,生纸写,不加装饰。皆有揩字注字处,急于自解而谢,不能俟更写。阁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。
愈恐惧再拜。
断桥流水西林渡,暗香疏影梅花路。蹇驴破帽登山去,夕阳古寺题诗处。树头啼翠禽,水面飞白鹭,伤心和靖先生墓。
春情
疏星淡月秋千院,愁云恨雨芙蓉面。伤情燕足留红线,恼人鸾影闲团扇。兽炉沉水烟,翠沼残花片,一行写入相思传。
道情二首
直钩曾下严滩钩,清风自学苏门啸。蜜蜂飞绕管花帽,野猿坐守烧丹灶。扁舟范蠡高,五柳陶潜傲,南华梦里先惊觉。
雪毛马响狻猊革占,神光龙吼昆吾剑。冰坚夜半踰天堑,月寒晓起离村店。一身行路难,两鬓秋霜染,老来莫起功名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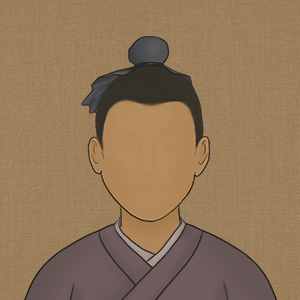 刘昶
刘昶 宋濂
宋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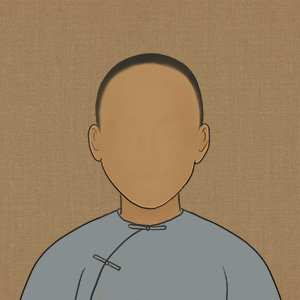 孟子及弟子
孟子及弟子 韩愈
韩愈 张可久
张可久 朱孝臧
朱孝臧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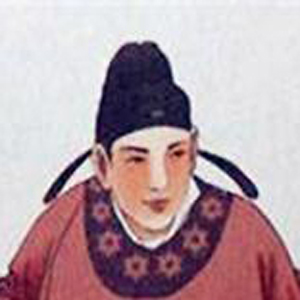 温庭筠
温庭筠 辛弃疾
辛弃疾 王炎
王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