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天地开辟啊曹魏代汉,如同日月重新放射出光芒。
陛下赐给我绝佳的机会啊,让我奉命前往辽东镇压叛乱。
本次征讨路上也经过了我的家乡,我定当奉皇命扫除叛乱,拿下辽东。
扫除万里江山的不臣之徒,整顿、治理这八荒之地。
大功告成后我将请辞告老,在舞阳安稳度日。
注释
重光:重新见到光明。
奉辞:奉君主之命。
遐方:远方。此句指奉命讨伐辽东。
逋秽:贬称流寇。
总齐八荒:意为整顿、治理所有的地方。“八荒”,犹言八方。
待罪:旧时官吏常怕因失职而获罪,使以待罪为自己供职的谦词。
舞阳:当时司马懿被封为舞阳侯。舞阳在今河南舞阳东南。▲
创作背景
司马懿在三国时期是魏国的大将,在与吴、蜀作战时屡立战功。公孙渊起兵反魏,魏明帝又派司马懿领兵讨伐。这样,他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权,为他的子孙代魏建晋奠定了基础。据史籍记载,司马懿为人“内忌而外宽,猜忌多权变”。对于他的为人,曹操曾有所察觉,还告诫过曹丕。但曹丕素来与司马懿交好,后来曹丕以至于其子曹睿皆比较信任司马懿,用他为大将。这也许是由于当时魏国的宿将大部分去世之故。但不管曹丕和曹睿对他采取什么态度,魏国统治集团内部对司马懿还颇有疑虑。同时,曹睿在位时,大权基本上还在皇室手中,因此,司马懿当时还不得不采取一定的“韬光养晦”手腕。此诗正表现了司马懿当时的那种心态。
(179—251)三国魏河内温人,字仲达。出身士族。东汉末曹操为丞相,辟为文学掾,迁黄门侍郎,转主簿。从讨张鲁、孙权。每与大谋,辄有奇策。曹丕为太子时,任太子中庶子,得信重。曹丕即帝位,封河津亭侯,转丞相长史。魏明帝即位,改封舞阳侯,任大将军,镇宛,平孟达之叛,三次率军与蜀诸葛亮对抗。齐王曹芳即位,与曹爽同受遗诏辅政,迁侍中、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。嘉平元年,乘爽从帝谒高平陵之际,杀之,为丞相,专擅朝政。死后,子司马师、司马昭相继专权。孙司马炎代魏称帝,建晋朝,追尊为宣帝。
见杨柳飞绵滚滚,对桃花醉脸醺醺。
透内阁香风阵阵,掩重门暮雨纷纷。
怕黄昏忽地又黄昏,不销魂怎地不销魂。
新啼痕压旧啼痕,断肠人忆断肠人。
今春香肌瘦几分?搂带宽三寸。
 司马懿
司马懿 李白
李白 王实甫
王实甫 毛泽东
毛泽东 向滈
向滈 秦观
秦观 赵令畤
赵令畤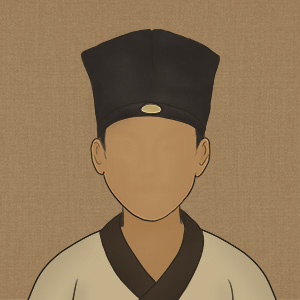 陈霆
陈霆 李好古
李好古 赵长卿
赵长卿 刘克庄
刘克庄